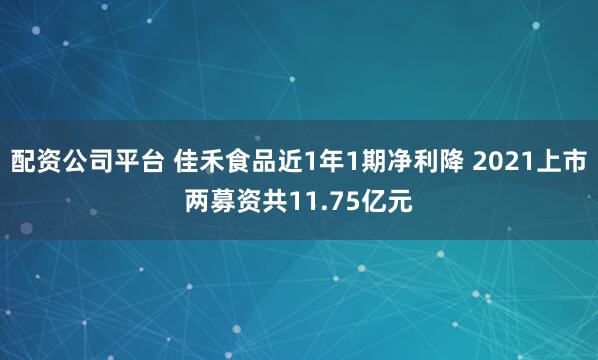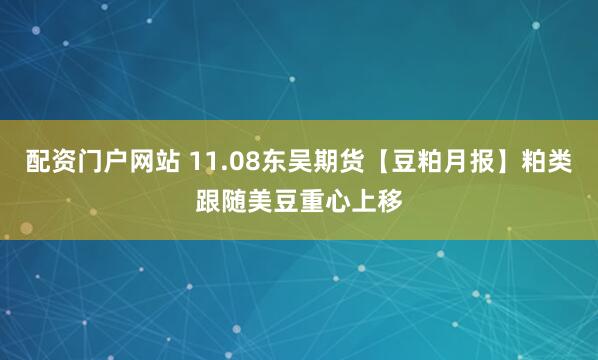2025年,这注定是一个钢琴与小提琴的“竞技之年”。从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音乐比赛、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到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再到备受瞩目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即“肖赛”),各种大赛的轮番上演配资门户网站,吸引了全球音乐爱好者、艺术家及业内管理者的目光。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消息之一无疑是美籍华裔钢琴家陆逸轩(Eric Lu)赫然出现在了“肖赛”的参赛名单中——这也让不少人感到疑惑。
毕竟,陆逸轩早在十年前便曾获得过“肖赛”第四名;20岁时,他便斩获了利兹国际钢琴比赛的桂冠,瞬间成为乐坛新星,演出邀约不断,且与华纳古典签约,至今已发行三张专辑。按理说,像他这样的音乐家,早已不需要通过参加比赛来提升自己的演奏事业,然而,他为何还要高调回到起点,再次与一众新人一较高下?这真的是值得深思的选择。
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陆逸轩的参赛动机。首先,肖邦比赛作为古典音乐界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赛事之一,拥有着无可比拟的商业价值和巨大的曝光度。每五年一届的“肖赛”,历届冠军如阿格里奇、波利尼、齐默尔曼等,都是当今世界音乐界的璀璨明星,金奖的分量不可小觑,堪称钢琴家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之一。而陆逸轩,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个机会,期望能够再次争取那曾经错失的桂冠。
与其说是为了再次证明自己,或许他还希望借此提升自己事业的高度,借着这个平台突破当前的瓶颈,进入超级巨星的行列。与之相对的是,曾在2018年获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小提琴家朱凯源,经过多年沉寂后重返赛场参加伊丽莎白比赛,却仅止步于第六名的尴尬结局。这一现实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尽管陆逸轩在音乐界早已拥有显赫的地位,他参加比赛所背负的心理包袱将远超其他参赛者,即便最终获胜,也未必能带来一场绝对辉煌的胜利。
展开剩余57%尽管如此,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朱凯源的失败并未阻止其他“前辈”们的选择;而每年不断有年轻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带着不同的梦想,毅然踏上了通往国际大赛的征途。我们看到,许多年轻选手甚至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投入到比赛中,有的人可能在赛场上征战十多年,始终未曾停歇。
就像今年刚刚夺得范·克莱本比赛冠军的沈靖韬,他的比赛生涯起步并不晚。早在2018年,沈靖韬便获得了吉娜·巴考尔国际钢琴比赛的亚军——这一比赛虽然低调,却拥有着相当的含金量。尽管如此,沈靖韬依然没有因此止步,而是继续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追求更高的艺术成就。就像杰努萨斯(Lukas Geniu?as)一样,虽然他在巴考尔比赛上表现出色,但最终使他名声大噪的,却是他在“肖赛”上的亚军奖项,以及他在2015年柴科夫斯基比赛中获得的亚军。
比较一下90年代曾获得巴考尔比赛冠军的美国钢琴家安吉利奇(Nicholas Angelich),他的经历似乎与如今的年轻一代大不相同。安吉利奇的独奏家生涯开始于获得盐湖城比赛的桂冠,随后他便通过纽约的首演与托马西尼乐评人的高度评价打开了知名度。与此相比,他并未参加任何其他大型比赛,而是通过演出与录音积累声誉,最终成为了钢琴界的翘楚。而同样生于1970年的另一位钢琴家沃格特(Lars Vogt),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利兹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得第二名后,迅速成名,并建立了自己的独奏家事业。
然而,今天的年轻钢琴家们似乎别无选择,许多人认为,参加“肖赛”、“柴赛”这些顶级赛事,是他们职业生涯发展的唯一途径。毕竟,像奥拉夫松那样没有任何比赛经历,却能够一举成名的机会,几乎是天方夜谭。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年轻音乐家们往往需要像运动员一样,拼尽全力,借助这些比赛的舞台磨练技术与技巧。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大赛所带来的曝光度与影响力,甚至是传统音乐会和媒体报道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每一场大赛的获奖名单上,常常出现一些令人陌生的名字,而那些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选手,他们真的能够最终蜕变为真正的“音乐家”吗?特里福诺夫(Daniil Trifonov)之所以成为“特里福诺夫”,并非因为他是“柴赛”冠军或“肖赛”季军,而是因为他自身的独特才华和不懈努力。
所以,或许我们也该思考一下,当前的“比赛至上”模式配资门户网站,是否真能造就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家?
发布于:山东省深金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